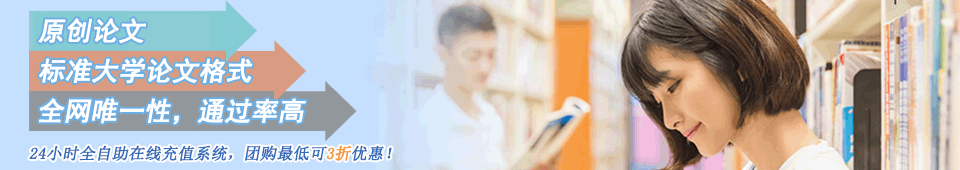恶意是描述心理状态的法律术语。《经济法律大辞典》[ 《经济法律大辞典》:恶意与善意相对,明知某种情形存在;与故意同一意义;动机不良的故意。]《法律辞典》[《法律词典》:恶意指行为人为获得不正当利益而损害他人的动机]以及王利明教授[王利明:所谓“恶意”,一是明知,二是明知且具有损害他人的意图,主观上有侵害他人的故意。《合同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梅瑞琦教授[梅瑞琦:恶意串通中的恶意系指意思主义的恶意,除须有消极的认识外,还需具有积极的意欲为必要。《论债权人撤销权与无效合同的选择适用》,《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 年第5期。]朱庆育教授[朱庆育:“恶意”系指双方共同故意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都对恶意的概念进行过解释。综合学者们的解释,我认为,“恶意串通”中的“恶意”包含不良动机的故意,不仅认识到其行为对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有损害后果,并对损害结果所采取的心理状态是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或者是有意识地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换言之,不管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这种恶意都是实际的、明确的。应当知道而事实上并不知道, 即构成所谓的“应知”的,不能认定为恶意串通。 (一)意思主义的恶意。 对于“恶意”的认定,应坚持意思主义。民法上的“恶意”有两种含义,一为善意之反面;二为动机不良之故意,如侵害他人之故意。此处之“恶意”,应为意思主义下的“恶意”,当事人明知串通行为会造成利益损害的结果,且积极追求之,具有侵害之故意。 首先,认定当事人的明知,即明知其恶意串通行为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以行为人串通时明知为准。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33号指导性案例及人民法院的判决,法官在认定“恶意”时均首先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串通人的“明知”。 指导性案例中,在认定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田源公司与汇丰源公司恶意串通时,根据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均对福建金石公司因“红豆事件”被仲裁裁决确认对嘉吉公司形成1337 万美元债务的事实是清楚的,认知国有土地及资产买卖会损害债权人嘉吉公司的利益。在人民法院的判决中,法官使用的“知悉”、“应该知道”等词可以作为认定当事人明知的表现。 其次,须认定当事人有积极侵害的故意,司法实践中不问当事人侵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原因和意图,只需认定其具有故意即可。 在司法实践中,“恶意串通”作为恶意串通制度在行为层面上的要素,应该从“恶意”“串通” 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考虑。恶意串通行为中串通人主观上的“故意”为主观心理状态,在举证及证明上较为困难,可通过行为人的外部行为来推断。当然这也为损害人的举证设置了更高的标准。通过司法审判分析,法院认定为恶意串通的案例,均坚持意思主义,认定串通行为人对其行为的后果明知、主观上具有侵害利益的故意。法院对要件予以分析,按以上两个步骤对当事人是否出于“恶意”进行认定。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定恶意串通行为中的“恶意”,不能拘泥于该行为在形式上的具体日期、行为方式等表象,而要考察该行为发生的背景情况、前因后果、是否有违正常逻辑或日常生活经验、是否有能够理解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该行为对其他有关民事关系的影响等因素,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是否不正当地损害了他人的利益等方面来综合判断行为的实质。此外,应该明确,过失的串通不具有“恶意”,过失的串通不应纳入恶意串通无效的范围,但过失的串通也会因行为违法性而被认为无效。“恶意”表明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为故意,即明知其所为的法律行为将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却依然有意为之。因主观心理不存在侵害的故意,并不积极追求损害结果的发生,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合同将损害利益的情况并不知晓时,则不能认定为恶意,也就不能适用恶意串通制度。恶意串通行为无效的规则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恶意,具有可归责性,过失的串通仍然承担与故意串通的后果显然在法理上存在矛盾,也不利于公平和合同争议的解决,所以不应将过失的串通认定为恶意,其法律行为一概判定为无效。 在司法审判中,对于过失的串通的判决相对较少,涉及到存在过失的串通时,法院认定一方或双方的过失虽然侵害了相对人的利益,但因无恶意串通、追求损害后果的故意,故不应承担恶意串通行为无效的责任,双方法律行为的效力及责任的承担应该按照其他规定予以处理。 (二)主客观结合的恶意 恶意串通为同一整体,“串通”为主观上具有恶意的相互配合或共同实施行为,“恶意”为双方行为时的均希望通过此种恶意行为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主观上共同意思联络、沟通。双方当事人意思一致的行为,即串通行为,若具有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恶意,便被评价为恶意串通行为。反之则被法律确定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是予以保护的合意行为。当事人具有的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恶意,若在客观上无串通行为,则不可能出现损害结果,也便缺乏归责的依据。 在司法审判案例中,法院适用恶意串通制度时,均将两者结合考虑。认定当事人行使串通行为时具有恶意,对于串通,形式较为多样,对于这些行为中“恶意”的认定,司法审判均将其与当事人的“串通”结合,主客观统一。 认定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关键是以当事人主观心态为主,但个人的主观心态属于个人内心的活动范畴,除了当事人自行坦白,他人难以直接查实或证实。如若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分配举证责任,要求主张权利的当事人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基于客观原因而导致举证不能,进而败诉的可能性较大,不具备可操作性。对于此类情况,应合理的采取推定方式完成举证或认证,即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或已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往日的习惯经验,推理、判断未知事实是否存在,并允许相关当事人进行反证、辩驳,只要存在高度盖然的可能性,则可择优判定某种事实,从而在最大限度内反映案件真实情况。 《证据规则》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在司法审判中,法官适用“恶意串通”行为裁判的状况大致如下:一、认定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的法律行为,该法律行为无效;二、不存在恶意串通或要求依据恶意串通行为认定法律行为无效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而不予支持。此两种情况在司法裁判中的现状为:在法院的判决中,后者远大于前者。 (三)是否以获利为必要的恶意 学界对于恶意串通行为的构成必须符合“恶意串通+利益损害”并没有太多争议。但对与第三种观点所增加的要件一一自己获利,其中多数学者认为无此必要。例如王利明教授曾提出,“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恶意串通订立合同多半是为了自己获得非法利益,同时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但是这并不是构成恶意串通的合同无效的要件,即使恶意串通合同的当事人没有为自己获利的目的,结果也不可能使自己获利,但是由于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仍然属于无效合同”。 当事人出于恶意,是否应以获得私利为必要呢?对此,存在两种观点。若恶意串通合同的当事人没有为自己获利的目的,结果也不可能使自己获利,但由于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仍然为无效合同。另一种观点认为,恶意串通行为以串通的一方或双方获取了恶意串通的利益为构成要件。 考察司法裁判,虽然当事人恶意串通订立合同多为基于获得非法利益的考虑,但法院认定当事人存在“恶意”时并不以“自己获利”为要件,考察的是当事人的明知、故意及对合法利益的损害。 不可否认,绝大多数“恶意串通”行为人在实施串通行为时基于自己获利的考虑,以“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来获利,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主动性,但在有些情形下,“恶意”实施的行为并未给当事人带来利益,甚至有可能损失利益。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恶意串通中,双方恶意串通转让债权的行为损害了债务人的利益,依据恶意串通行为适用被认定为无效。双方当事人串通,以低价损害转让财产,受让方获利,但对于转让方而言,低价转让的方式使其损失利益,而非获利。 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形:当事人双方均不为自己的利益,纯粹为了损害第三人的利益而订立合同,其主观上具有“恶意”,合同应该适用恶意串通行为认定为无效。 综上所述,恶意串通行为的“恶意”非以获利为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