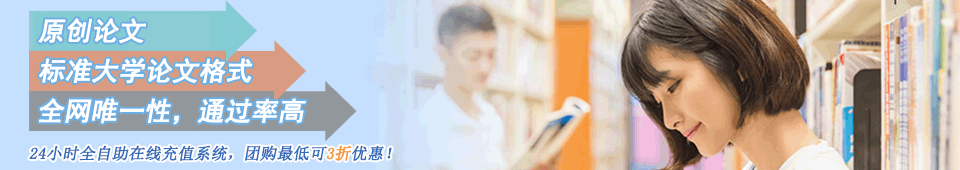(一)第三人的界定 1.第三人是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主体。 第三人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所谓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其实施恶意串通行为的是合同当事人,所以此处所指的利益受到损害的集体或者第三人是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主体。如果合同中的数个当事人恶意串通,但仅损害其他合同当事人的权利而不损害合同以外的其他人的利益是,则属于其他原因以确定合同无效或者确定为可撤销合同的范畴,而不属于以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为由确认无效的范畴。 2.第三人是特定的主体或者不特定的主体。 在司法实践中,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分为两种,一种是特定的第三人的利益,一种则是不特定的第三人的利益。前者是本文所提的第三人利益,而后者则不是,在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不特定的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实际上当事人所损害的是社会公共的利益,应当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为由确定合同的效力。因为如果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的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利益是,该不特定的第三人无法主张其权利,所以需要由国家来主动保护其权利。 (二)第三人利益的甄别 1.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可以限制民事权利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在抽象的层面上可以将民法上的国家利益具体化为以下三种类型:其一,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经济利益;其二,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政治利益;其三,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安全利益。国家利益往往侧重于国家的政治利益,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我认为,对是否存在有不同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利益的争议实际上涉及民法上的价值判断,在私法领域内,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确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将民法范畴内的国家利益归入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2.集体利益。集体、集体利益、集体所有权等一系列词语,与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的集体所有制存在着密切联系,集体利益中的利益主体“集体”本身并不是一个纯正的法律术语,对其内涵的界定也众说纷纭。这就使得集体利益究竟是作为一个实体化的利益,还是作为一个与社会公共利益处在不同层面上的集体公共利益的简略表述,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在国语中有时可以将集体理解为与之相似的公共。若对公共利益这一抽象概念本身做抽象和具体、整体和局部之分,即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整体利益还可以不断分类下去,那么集体利益代表的便是一种具体的、局部的公共利益。然而在我国法上,集体经常被限定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是一个具有某种实体意味的组织,这与不具有实体意味的公共明显存在差别。即使将集体理解为一个局部的公共利益,也存在相应问题,比如这个局部有多大,是大至整个国家还是小至在任何一个团体中共同利益,又比如公共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产生与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密不可分,实践中也常常混淆。这便导致一个不可回避的困境:我国法律对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加如此重点之保护,就无法保持不同所有权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对这一问题,我倾向于认为,我国民法所保护的集体利益其实是作为一个公共利益的另一种表述在法律中存在,保护集体利益就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以此为出发点,社会公共利益是可以替代集体利益的。 3.第三人利益。作为利益主体的第三人,泛指相对于实施法律行为当事人以外的一切民法上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此,有学者倡导要区分第三人利益为特定第三人利益与不特定第三人利益,以此认为立法规定的“第三人”并非指个别的私人,而是泛指一般的人,对“第三人”的利益损害,将直接导致对社会利益的损害。换言之,不特定第三人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表现类型。但如此区分问题也随之而来,比如某些情况下,对特定第三人利益的直接损害,也是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间接损害,在此情形下不应排斥以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保护特定第三人利益。所以,即使根据法解释学的目的性限缩论将第三人利益解释为不特定第三人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问题仍然存在。
我国民法上的恶意串通的规定溯源于前苏联民法,又与虚伪表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旨在通过对动机违法的法律行为给予否定评价实现对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或许正是因为当初的立法者企图以该条款既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又涵盖意思表示瑕疵的相关内容,反而使恶意串通之规定在内容规范上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在逻辑结构上也呈现一定的不合理性,这一中国民事立法的特色规定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举证上的困难导致实务中对恶意串通的认定很少,本文从恶意串通构成要件分析了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认定通过对指导性案例及收集到的司法裁判的分析,法院在认定当事人是否实施了恶意串通行为、是否以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但就恶意串通的认定,就可以分为“恶意”的认定、“串通”的认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的认定,本文仅是对该司法裁判问题的部分予以分析。要对恶意串通制度在司法上的适用做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恶意串通制度在其构成及认定上较复杂,各要件都存在很大的分析空间。基于审判实践的视角,恶意串通制度中的“串通”,主观上应从意思表示的角度予以认定,无论明示或默示的内心意思表示均可构成串通,在客观上当事人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实施了该恶意串通的行为。“串通”的形式多样,恶意串通作为一个整体,认定时应将“恶意”与“串通”结合恶意串通举证困难、认定复杂及与相关规范存在竞合使恶意串通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出现尴尬———因证据不足而不予持的状况太多。关于恶意串通制度在立法及法律解释上的完善仍有很大的空间。。由于当前对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认定的研究成果较少,受知识范畴和分析研究能力的影响,开展这一范式的研究压力很大,对文章的质量难免存在忐忑之心。仅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推动我国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认定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