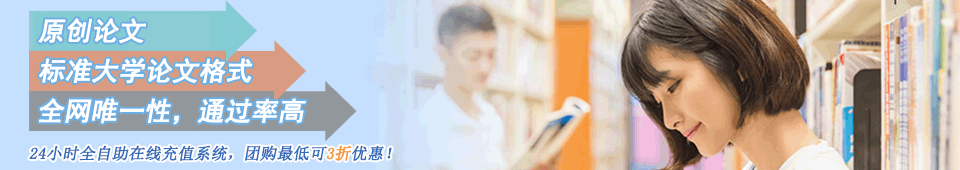主体能动性可以破除有限的时、空,激发Th命创造活力 1.“心外无物”的主体性特征有利于调动主体能动性 前文在论述王阳明的“心即理”与“心外无物”思想时,均言及不能离开道德主体(或主体“心”)的实际践履,简称“道德实践”。这种道德实践具有真实性的特点,因为这种学问并非是教导人们先树立一个研究对象,再做出态度、行为等反应,也不是让人们一昧地服从社会的道德规律,而是依据主体“心”之觉悟去实践,再依此实践来提升觉悟。换言之,在王阳明那里,道德主体的“知”与“行”是相依而进的关系。若要进一步作出论证,还需返回到“心外无物”思想的两大特征,即主体性和过程性,主体性便反映在主体觉悟上,过程性则反映在道德实践上。总的说来,人依循自己的觉悟去实践,这相对于依循既定的义理去实践而言更能体现人内心真实的想法,即立足于主体真实的情感经验,有利于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 在这里,“觉悟”与“实践”两者是相依而进的关系,又因为“觉悟”内在于人心,所以人的“实践”每扩大一步,“觉悟”也就跟着扩大一步,当“实践”遍及家庭、国家、宇宙、历史中时,此中一切亦为“觉悟”所涵摄了。至此又产生一个问题:它和马克思提出的辨证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世界观有何不同呢?我认为至少有这样两点不同:一,终极目标不同,前者是为了“成德成己”,成就道德人格,后者则是为了认识世界,进而改变世界;二,思维方式不同,前者是“和”的思维方式,后者则是“分”的思维方式。 2.“与天地参”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 当人从自己内在的觉悟去进行道德实践时,便会明了所为皆是在尽自己的心性,而人对于外在世界的一切道德实践行为都依赖于人想要尽自己内在心性的愿望,这一愿望必须要实现,它是心性自身的要求,甚至不容于自己,类似弗洛伊德所讲的“超我”人格。弗洛伊德曾从“我”的人格中剖分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重人格,“本我”是人无意识的主要部分,它只遵循快乐原则,无所谓道德性; “自我”负责连接“本我”与现实世界,它从“本我”中汲取能量,调停现实世界与“本我”之间的对峙;“超我”由“自我”分裂而生,但它已不受“自我”控制,象征着良心等至高至善的德性,负责执行心中的道德律令。[12] 由此可分析出,道德实践还涵有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是指超越现实的自己,通向的是天人合德的内圣之路。道德实践所涵的超越性要想真正实现,必须依赖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进一步讲,人唯有尽自己内在之心性,才能够“与天地参”,即“明心见性,以达于天”,这和孟子的“尽心知性则知天”有异曲同工之处,于此亦可见王阳明对孟子的传承。 3.“与天地参”所获得的超越性可以破除有限的时、空 人与天相通后便获得了一种超越性,可以超越现实之自己的有限,现实的人的有限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归纳起来讲,可以说有自身造成的有限以(内)和外界造成的有限(外)两种,而这两大类原因之所以能导致人的有限,究其根源,则是它们受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规定,时间属性与空间属性自始至终都贯穿于人的活动之中,同时也限制着人的活动。 以空间对人的限制为例,“ft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ft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ft小月更阔。”此诗为幼年王阳明所作,题为“蔽月ft房”,这首诗的有趣之处就在于,通过选取不同的参照系或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同一样事物,人们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结论,这便属于空间对人的限制。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限制”不能单纯地作“束缚”解,因为“限制”本身也在充当着人存在的支点(或坐标)。 那么世间是否会有能逃离时空法则之物?我认为人类的思想就有跳出时空这一维度的可能,但前提是这种思想不能是纯经验性质的或者纯常识性质的,因为这两者正是以时空为其经纬的。上文在讨论“心外无物”的哲学倾向时已经提到,哲学思维方式作为看待世界的三种基本方式之一,具有反思的特性,而当思想的这种哲学式反思臻于极致时,也是没有一个支点的,因为任何支点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和再反思。 但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所言及的,人不能怀疑我正在怀疑这件事本身,因为人若怀疑我在怀疑,那么其实还是在进行怀疑这件事,所以反思至极致时其实也还是有一个支点的,王阳明将这个支点确立为具有至善性和完满性的“心”本体。“心”本体“与天地参”,能够破除时空带来的限制,是激发人类原始生命的无限创造力之源。探索与创造是生活最高的目标,人类跨越时空找寻过去积累的财富,以自己的方式上下而求索,尝试内化其中对自己意义重大的部分,通过这种探索与创造,人也可以为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自己定位。 (二)意义之源的“心”将物我合一,丰富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1.“心”将人与自然合一,消解了主客体之间的对立 天地本无心,但在王阳明以“心”为体构建出的意义世界里,人可为天地立心。作为天地之心的人,既可以是当下的存在,也可以是本然之体的存在。[13]王阳明“心外无物”思想中的“心”指“本心”,“本心”具有超越性,它超临于时空之上,是恒常的、真实的,因而本心也是一切意义之源,它通过主体的自我觉悟与道德实践构建起“我”与“物”的意义关系,并以此诠释这个世界,或者依其所诠释的世界展开道德实践。 此处“本心”的主体是指道德主体,而非认识主体。之所以将认识主体与道德主体加以区分,是因为从这一区分钟可以看到中西两种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认识主体表明主体自身是在从主客对立中把握人,按照物质实在来了解人,而道德主体则表明主体是在从主客合一中把握人,把人置于宇宙发展的中心,在物质、生命、心灵或精神的统一中了解人。 2.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促使生命精神向自然回归
根据对王阳明“心外无物”思想的解读,可以这样认为: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关系,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离开人的心灵将失去存在的意义,人与自然是合而为一的。虽然这一观点明显带有主观色彩,容易落入唯心主义轨道,但是亦应看到其合理的一面,即它解除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人成为自然化的人。自然人化后文明开始出现,人自然化后则可以与自然相感通乃至达成理解。 人与自然的合一也意味着人可以将自己的精神意志灌注于自然万物之中,但这并非是对自然的绝对主宰,而是一份对自然的生命精神的感悟。原始宇宙“包含生命与物质,而精神即潜存在生物之生命中......只有人类独保存原始宇宙中物质生命精神之一体,而精神性特显露,遂发展而成今日之人类。”[14]人本就源于自然,所以人与自然的合一也可以理解成人类的生命精神对自然的回归,这种回归是人与自然相分后站在更高层面的精神性的回归,至此,人才真正回到自己的本性,成为宇宙间真实的存在,而自然已被至于人的本心本性之内。因此,人面对自然发挥主体能动性时,依循着自然的本性其实也是在依循着人自己的本性。
结语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与西方的心理学科学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前者着眼于价值层面,后者着眼于事实层面。心理学把人的自然的行为当作经验科学研究的对象看,进行的是纯事实的研究,不对人的心理行为作任何价值的估量,我想这可能与西方的哲学传统有关,“传统哲学中之理性的灵魂论将人心视作一实体,而论其单一不朽,自存诸形式的性质的;西方之认识论,乃研究纯粹的理智的认识心如何认识外界对象,而使理智的知识如何可能的;西方一般之形上学,乃先以求了解此客观宇宙之究极的实在与一般的构造组织为目标的。”[15]前文在论述“心外无物”思想的哲学倾向时已指出,“心”与“物”体用一如的关系将模糊“心”与“物”的界限,不利于知识论的建构。 我认为这种状况带来的最不利影响就是使中国文化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真正的科学是为求知而求知的,即动机已超越了实用层面。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在器物制造、农业技术、天文、算术、医学、地理测绘等方面的水准要高于西方,可见中国是重视这些科学实用技术的,也是不乏科学智慧的,但是这些实用技术竟无法再继续展现出质的飞跃,不禁让人感到疑惑,通过对王阳明心学体系尤其是“心外无物”思想的分析,这一疑惑或可得到一二解释。心性之学被视为中国文化学术的核心,它也是人道德实践的理论基础,道德实践起始于道德主体的自我觉悟,落脚于对客观世界的价值判断和主体内在的道德修养。既已止于主体内在的道德修养,即道德主体只是向内收缩,那么“正德”便失去了向外(“利用”)通的门路了,所以要孕育出科学精神就需要收敛道德方面的目标,而要收敛道德方面的目标不仅需要个体自觉成为道德的主体,还应自觉成为认识的主体,并且要在这两个主体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不至于二者混沌不分,要想自觉为认识的主体也依赖于这条界限。 作为中国文化学术核心的心性之学有着道德的底色,道德精神对于涵养个体内在人格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不能因此就忽视了由于囿于道德圈子而带来的弊端,“心”之本体既已突破了时空的规定性,为激发生命的无限创造力提供了可能,那么便不适合再让向内探求的文化理想成为孕育科学创造精神的阻碍,所以吸收其中的合理内核,扬弃与时代脱轨的部分至关重要,这也是其在新时代继续发展下去的前提。现代化中国的实现依赖科技创造,科技创造局面的全方位打开既有赖于制度层面的完善,当然也需要真正的科学精神作为不竭动力。 |